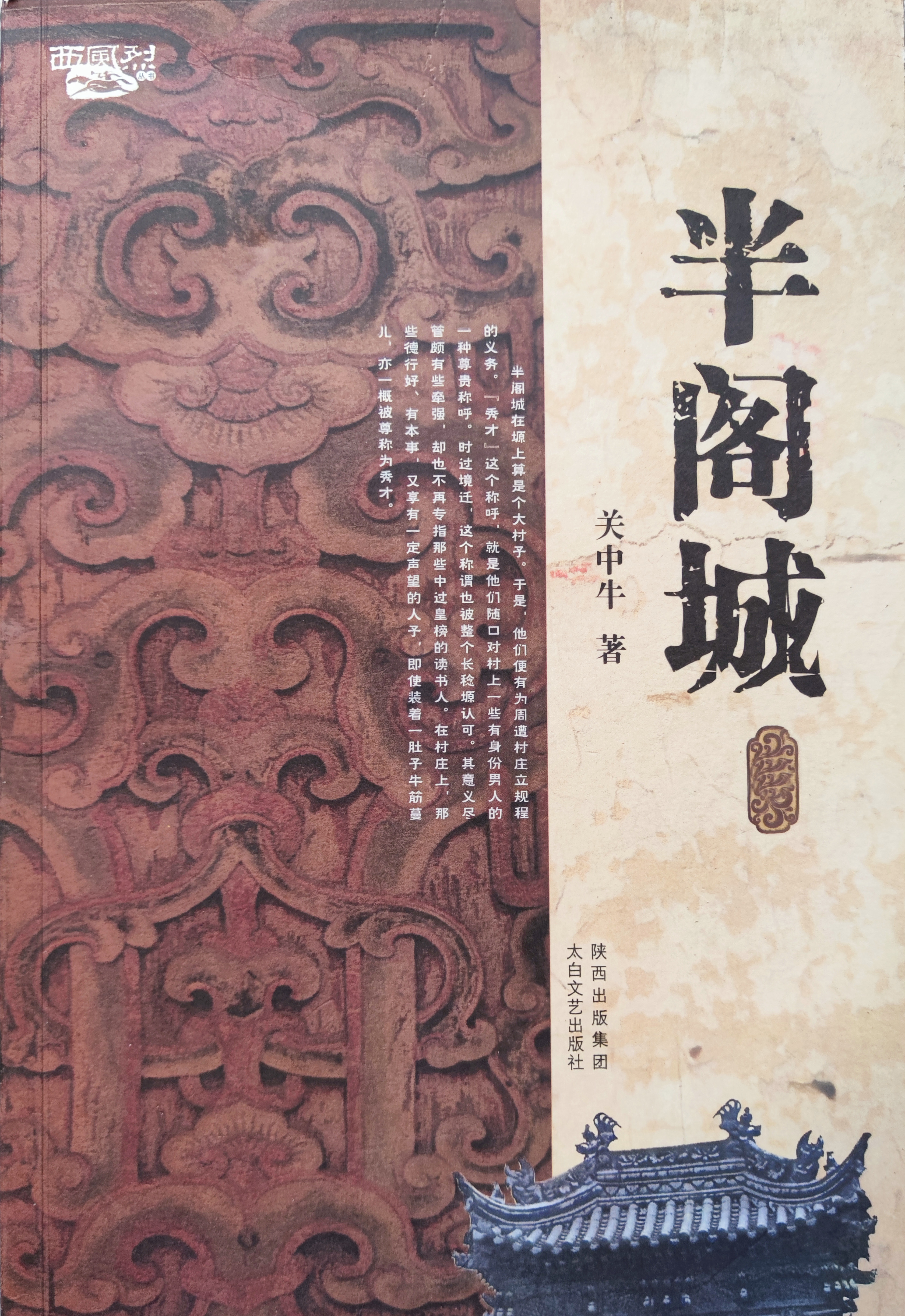
-
半阁城
本书由鹿阅读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
日子(代引)
山里的日头比山外短。从东山兀自钻了出来,刚近西山又一骨碌滚落下去,中途只有两顿饭的消停。留给田头地脚一些斑驳的树影,久了便在石头上生了青苔,被山民们奉做一个叫“日子”的东西。冬暖夏凉,春华秋实,一天天不请自来,又一天天就这么在不经意中过活着。曾经的那些数不清的日子,如果能拣拾着摞起来,绝像山民们每顿饭必端的那一只只耀州瓷老碗一样平淡而无奇。
眼下是初夏的天气。长稔塬上的人们早上出门还穿着棉袄,刚抡圆了䦆头又得光起膀子来。这是被山民们称为三变脸的日子。接近这个日子前后,塬畔上的麦苗便开始吐穗扬花。从南方飞来的布谷鸟已经站在柿树的枝头夜夜鸣叫,拼命地向人们提醒着这个季节。
天色刚放亮,东方隐现出一丝鱼肚白儿,太阳便跳出了河岸。瘸着一条腿的村支书高运喜架着拐子,骑着一辆破“三枪”自行车刚从公社赶了回来。这头刚到村头,却远远地看见佑普爷一个人在东城壕转悠,他便跳下车子大着声招呼地问道:“爷,你转哩嘛?”
自打前年夏至那天,他老人家吃过后院树上掉下来的几颗熟透的烂杏,不慎得上那个叫做“鸡鸣泄”的贵恙,每日里的清晨,当老爷子家里那只芦花公鸡喔喔地叫过头遍,全村那些老公鸡、小公鸡附和着高一声、低一声一齐鸣叫起来的那个特殊时辰,老汉就得按时按点起来,赶着紧儿去完成每日里这门必修的功课。村庄里那些早起拾粪的人,时常会看到老爷子不及出城门便已提着宽大的裤腰一路匆忙地向东城壕小跑,耷拉在他脖颈上的一条九色棉线辫的裤带,随之摆动得如同宋王爷的帽翅般英武。
听见有人远远地招呼,老汉忙收住一脸尴尬,哭笑不得地应承了一声,“嗯,是喜娃。你咋才回来?”
高运喜在路旁撑好自行车,取下拐子架在夹肘窝里一瘸一拐地向城壕这边走,嘴里不住地自顾嘟囔:“公社刚放人喀,紧赶慢赶还是热了一身臭汗。你一个人在这儿转啥哩?”
佑普爷没有吭气。待他走近了,这才无声地递过手里那杆抽得正旺的烟袋锅子,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运喜接了烟袋,用手顺着那玉石烟嘴儿胡乱抹了一圈便噙上嘴紧吸了几口。
此刻,老爷子却突然开口问了他一句:“嗯,公社这回又给了个啥章程?”
运喜接过烟袋吸得太急,不小心抽了一嘴烟油子,紧着吐了几口苦水,讪笑着说:“呸,还不是让报产的事嘛,呸呸。狗湿的一伙二杆子民兵,三天三夜不歇火逼着让人说胡话哩,不报不放人喀。开始,他们还嫌咱们村报的比人家少了一大截,几个人围了我一夜,要是再不答应,人家就准备组织人专门来拔我这杆‘白旗’哩!”
佑普爷却无心听他那些废话,随便地问了他一句:“你给人家报了多少?”
运喜轻省地说:“嘁,嘴上报哩,又不是让地里产哩。我先报了六百万斤的总产,劈头挨了俩耳光,我一看苗头不对,紧赶改口说力争一千万斤。嘿嘿,要不,那伙子二毬货真下茬打呢!”说完,他居然讪讪地笑了。
老爷子并不关心他在公社挨耳光的事情,只是关切地问:“一千万总产?那亩产应当报多少?”
运喜嘴里自顾说:“我也没顾上算计,起码得一万斤往上点……”
老爷子又问:“一万斤?从古到今,谁见过一亩地打一万斤麦子的怪事情?今年这号庄稼,连麦秆拔下看上得了一百斤么!”
运喜苦着脸说:“不行呀。人家报纸上有个‘四季青’公社,据说有一亩样板田已经达到十二万斤了。咱们这里虽是旱塬,亩产咋说也得一万往上点。张书记说,这已经是很保守的指标了。”
老爷子知道,眼下这些邪性事情也确实不是他和瘸子说了算的事情,又关切地问了他一句:“会上,公社说没说食堂的事?”
运喜皱着眉头,吃力地咳嗽了一阵子才说:“唉,坐了一场子人,个个肚子里都明得跟揣着一面镜子似的,可谁敢言喘嘛。各村都还硬撑着哩,公社一时也没啥新说法。再说,那个场合咋敢提说这号话茬?是个傻子都知道,明摆着那不是狗咬石匠——寻着挨錾呢!”
看着老爷子虎着脸再不说话,运喜这才又提说起另一件令他十分头疼的事情和老爷子商量:“爷,昨天后晌,张书记大会总结时强调说,炼钢工地还要抽劳力哩。让各村继续伐些大树赶紧煨木炭,这次上交任务比上次可能还要大些呢。”看到老爷子没有接茬的意思,他只好又自嘲地说:“啧,啧,真是胡日鬼哩!铁匠炉用面煤都烧不红铁疙瘩,木炭火咋能化开矿砂嘛?咱们给钢厂交的那些烧结了的炭渣疙瘩人家根本没验上,让派人去拉回来再炼一遍。那玩意儿咋个好重炼嘛,还不如再拉些矿石……”
听运喜说到这里,佑普爷叹了一口气,这才接着他的话茬说:“交就交呗。全村都没几棵老树了,我看下一步还把城门拉去煨木炭呀!眼见已经吃光了库房里那点种子,往后让食堂的炊事员往锅里给社员煮啥呢?!”
运喜也不接他这话茬,自顾叹了一阵儿气,这才给老爷子回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唉。这几天,在公社受训没把我这颗脑子训出啥长进,一个人倒是闷出个馊主意……”
老爷子一听从支书嘴里蹦出“主意”这两个字,无心地搭讪了一句:“眼前这号摊场,你个瘸子能有啥好主意嘛!”
运喜眨巴了一下自己那双小眼睛,十分诡秘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老爷子蹙了一下眉头,忙问:“你是说——食堂?”
运喜肯定地说:“对。看来,硬撑已经不是办法了。明着散伙吧,上边不给唔个精神,你我到时也吃罪不起喀。我想,咱们不如……先给各户偷偷安个锅灶!”
佑普爷倒吸了一口凉气,思谋了片刻才说:“啊呀喜娃,这,这,你不怕去坐牢哇?”
运喜这时才不慌不忙地坏笑了一阵说:“爷,你这老汉关键时刻还真不糊涂嘛。唉,让去坐牢又不是让去坐花轿,这事闹不好就是惹火烧身的事喀。可咱首先得想个周全的办法把人命先保住吧?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村的沟地这么多年撂荒不少,你说,能不能变着法让社员自己开垦点?”
还没等老爷子开口,他紧接着便把自己那点小想法在老爷子面前满盘满碗地端了出来——“当然,真的要这么直戳戳划地,当然也不是个周全办法。咱可不可以先以维护集体利益的名义,把社员现在的自留地统一收归大田,然后让各队给各户划到沟坡,一收一放!”
佑普爷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嗯。有爷这把老骨头给你撑着,你说咋个闹法?”
运喜估摸这事只要老爷子认可便十成有了八九,立时放下拐子,拜倒在地给老爷子叩了一个响头。
他那腿脚本来就不咋灵便,跪下去时倒是挺利索,趴在地上后自己却一时站不起身来,嘴里依然给老爷子不住地安顿着说:“爷,你先把喜娃这礼程收下。过后就是杀头坐牢,我也绝对不会牵连你们。主意是我出的,事情万一闹湿塌了,总得有个人去承头喀!”
佑普爷一看,一个瘸子趴在地上老半天不起身,他立马怒喝道:“起来!一个党员的膝盖咋这么软?新社会还行这老礼数闹啥?”
运喜被老爷子扶了起来,依然忍不住哽咽地说:“爷,心香还年轻,几个娃娃还都小……假如将来闹出啥闪失,还托您老在村院中多多关照他们一下。将来我如果报答不了的话,只好让儿子们替我给您老抬棺送葬……”
老爷子却不领情地回了他一句:“我还不想死呢!”
运喜嘴里却依然咕哝着:“我这回也真他妈想通了,啥叫党员?紧要关头不站出来替社员谋生路、整天跟着那帮人一起睁着俩眼说瞎话,那还叫党员吗?我就不相信,人民公社就是让社员整天去喝糜面糊汤煮榆树皮?!”
佑普爷脸上终于有了点舒展地说:“行啊。真没看出来,你们高家人老几辈还能出一个硬崽娃。不过,各家各户的煮饭锅都上缴了钢铁任务,咋让社员重新开伙嘛?再说,眼下粮食就是个关口,总不能把仓库那点种子给社员借出来糊口吧?”
运喜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胸有成竹地说:“爷,这号事情依我看就不用咱们熬煎了。前几天吧,有人给我反映过保管员谢善广在食堂烧萝卜吃的事情,不管大小总是个事儿吧?外村有些干部在集体食堂搞特殊化开小灶,已经被公社抓了典型,咱们也不能冰锅冷灶的啥问题也没有吧?我看咱就从这事入手,先开个批判大会羞臊一两个贪嘴的货色!”
佑普爷更加奇怪地问:“羞臊人能抵一村人肚子饥饿?”
这个时候,运喜那蔫坏的脾性立即便显现出来了,他故意卖着关子说:“看看,你这文盲老汉一点都不懂得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他老人家经常教导我们说,要相信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你咋把这个闹革命的‘老基本’都忘了?据我分析,村上眼下还没有绝粮。就在前几天,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学校高先生发现有些学生上课偷吃炒豆儿,他开始收过几把,也没批评娃娃。后来,自己把收来的豆儿自个吃了。那些胆子大一点的一看没惹出事儿,就经常给老师往抽屉里偷偷放一些炒豌豆、蓖麻子、棉花籽,反正样儿倒不老少……”
说到这里,他更加神秘地说:“爷,这才是最近的事儿喀。这说明啥问题呢?说明有些社员家里还真有点垫底的东西哩。入社清粮时,咱村都是社员自己报了斤数自己往食堂掮,咱们成立的那个搜粮队也是做了样子喀。你想,谁家缸里瓮里坛儿罐儿还不留点糜儿豆儿?当时我心里还想过,只怕日后这集体食堂越办越红火,公家拿卡车运来的大米洋面一时都吃不完,他们就是来主动上交我还不想要他那点陈粮呢。现在看来,当时那点小疏忽还真是个好事儿……”
两人站在那里正在商量着,这时候,村上的二流子羊倌詹木林赶着羊群下沟路过地头,他远远地看见支书在地头和老爷子说话,给这边打了个招呼,老爷子和高运喜便停止了说话。
羊倌是个外乡人,几年前在半阁城做了上门女婿。只见他一路响着羊鞭走近地头,看见支书和大队长在那儿说话,这才停下脚步用他那不会打弯的舌头招呼着——“高,羊吃草嘛,可以饱的;人的胃嘛,扁扁的。”说罢,他像个马戏团的小丑似的双手一摊耸了耸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站在那儿再不移步。
看见高运喜并没有招承,他又接着说:“真的,你发的三十斤粮食远远不够,现在我还有老婆孩子嘛。明天,你得给我提前发下一个月的粮食。”
运喜一看这货站在那儿不走,只好远远地搭理了一句:“今日才十几嘛,吃了下月口粮咋办?总不能让你这鳖犊子后头喝风胬屁去?”
詹木林依然停在那儿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不会的,不会的,那我只好再借下一个月的……”
运喜只有苦笑了。
对于这号不解世事的洋荤子,他也没办法解释,又不好得罪,只好打发他说:“借吧借吧,我一会儿给保管员打声招呼,看能不能先给你装点黑豆和苞谷搅和着对付几天……”说完这话,他自己又嘀咕了一句:“我看让你龟子怂把种子吃完了,秋里让社员种啥去!”
詹木林一听支书这么爽快地答应了,便乐呵呵地说:“又是黑豆吗,奴,奴,这次不要!那个粮食吃了,人的肚子会生气的。你们都知道的,麦秀又要生小宝宝了,她说要吃荞麦做的踅面!”
一听这家伙在那儿居然还得寸进尺了,运喜就没好气地又重重地给他丢过去一句:“踅面?坐个破月子恁娇贵?她这阵要是想吃人肉那倒好办了,让我把这条腿剁上给你老婆煮嘛。食堂眼看都开不了伙了,你们还挑三拣四的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阵子,你让我给你屙一口袋荞麦去!”
两人离得远,詹木林并没听清楚他丢来的回话,只听见有“一口袋荞麦”那句话尾巴,便十分高兴地招呼道:“那顶好的,顶好的,我放羊回来嘛,就拿口袋来找你签字……”
运喜再没有心思和他搭话。
佑普爷却被老詹站在地头那个认真劲儿逗乐了。
洋相
詹木林是半阁城一个大活宝。他至今没有入社,也从未和大伙一起收种过庄稼。这倒不是他人懒,委实是这货一点儿都不会作务农活,每天只会赶着自己家里的几只羊满沟转悠。据了解其底细的人说,这个说话口音古怪的外地客老家在新疆。此前谁也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更懒得记那绕口的县份。总之,那地方十分遥远。
说也奇怪,别看这家伙平日说话结巴,人也显得窝窝囊囊,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据把这货攀扯来的高支书给村民讲,老詹年轻时不但上过大学,在朝鲜战场上还做过总部首长的贴身翻译。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厮原本分配在山东一个叫青岛的地方做着大学教师,大前年趁着暑假有点闲空,他跑到半阁城专意来探望了老战友高运喜一回,居然萌生了不再回城的念头。不久,便背着铺盖死乞白赖地迁来半阁城,做了一个闲汉。他的这个举动,也让这些山民们见识到了,眼前这个世界还真有这样的浑球儿!
村上来了这么个外路人,开初那阵大伙儿还把他当稀罕待见,久而久之也渐渐失去了新鲜。可是,由于他的到来,却给村庄上原本秩序井然的辈分排序带来了一点称呼上的混乱。此前,无论村民们相互之间的年龄有多么大的悬殊,人人在村庄上都拥有自己应有的辈分。即就是谢、高两大姓氏之间,按照各自的名字也可区别出辈分大小。对于老詹这个外地人,老少爷们见了他只好按照相互间的年龄,一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