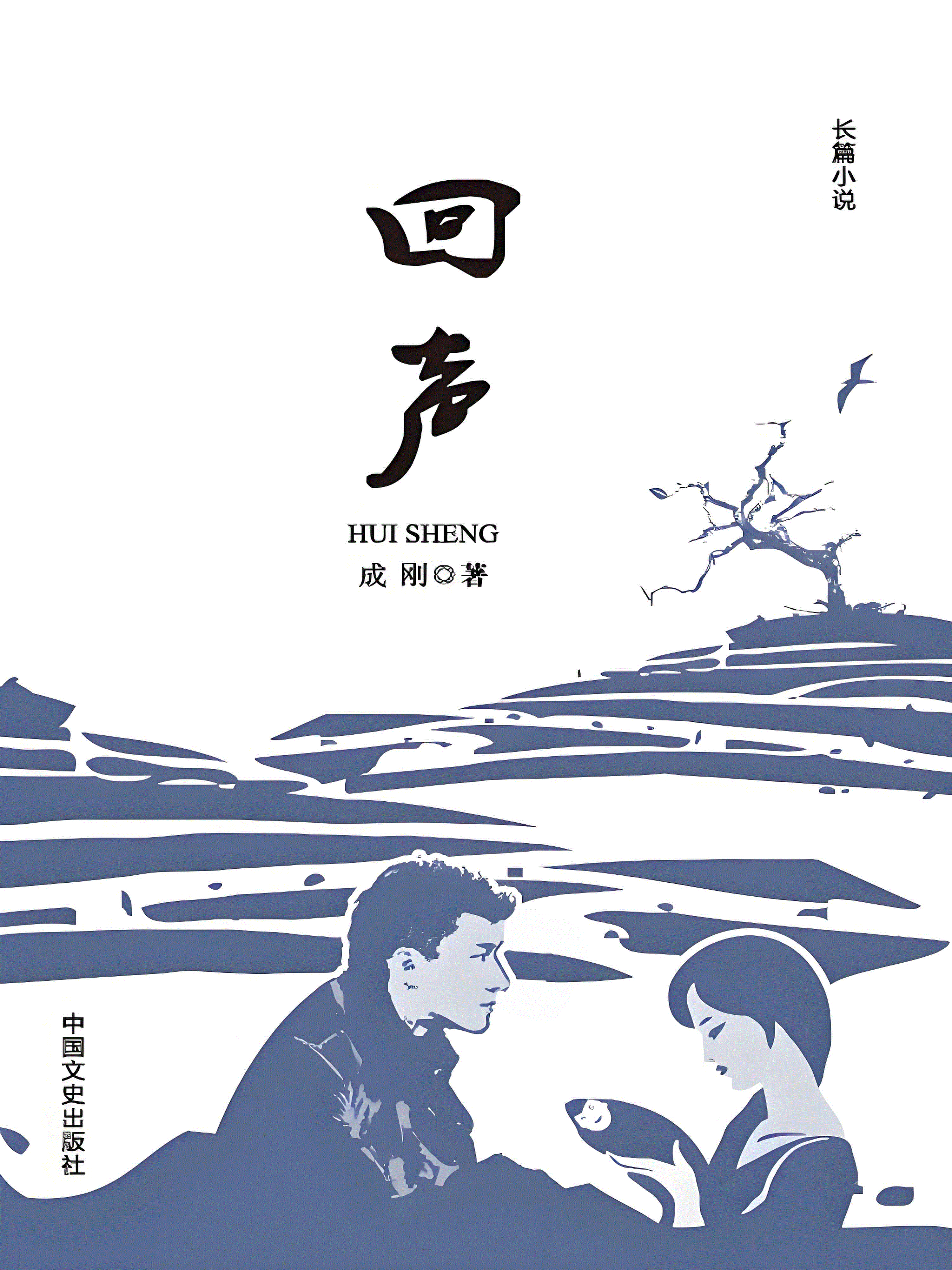
-
回声
本书由鹿阅读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篇 第1章
在我们幼小蹒跚学步的时候,经常被自己的影子吓得抱头鼠窜,长大后才知道,那其实是太阳光把我们投射在地上的另一个自己。太阳把我们定格在这个时代,定格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我和庄宝盒风马牛不相及,但人们还是十分习惯地把我俩联系在一起,这大概源于我跟他从小是同学和邻居,长大后又同娶了牛家的姐妹。
我叫何书盒。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后一晚十一时出生,正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差,让我跻身五零后而不是六零后。身份是学生,初始文化程度高中。
我俩的出生地相距遥远。他出生在遥远的青藏高原,我则出生在蒲松龄的故乡,据父亲说离蒲家庄只有百步之遥。
后来我俩阴差阳错地做了邻居。在说到各自的孩子时,两家母亲都把起名字当成了笑话。
庄宝盒的母亲榆叶说,当年她怀了老庄的孩子,足月前星夜兼程赶往丈夫所在的部队。那时候家乡正大炼钢铁,闹饥荒,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连生孩子都没劲儿,孩子赶在部队里出生,至少可以吃上饱饭。但是行至半路上宝盒子就急不可待地要见他英雄的父亲了,于是生在了进藏的卡车上。
进藏的时候正是初冬,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庄宝盒哇哇坠地,连个暖和的地方都没有。司机于大哥脱下油乎乎的军大衣把他裹上,又找来个盛工具的木头箱子把他搁在里头,这才保住了他的命。他安然于睡梦中进入海拔三千米的青藏高原,等父亲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抱出他来时,他竟用一泡热乎乎的尿液和响亮的哭声向打扰他温柔梦境的老庄表示抗议。
娘说:“多亏了于大哥的军大衣和那只破木箱子!”
老庄朗声地大笑道:“老于你就甭谢了,他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盖得是我的花被子,这算扯平了!至于这只木箱子,我得保留起来,这哪里是只破木箱,简直就是个宝盒子,给我送来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
于是,这个生在冰天雪地里的孩子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庄宝盒。
而我的出生完全不跟他一个版本,我出生在书香门第。
据民国版的《何氏家谱》记载,我爷爷的爷爷是清末举人。他七次会考都无果而终,愤懑之余用毛驴驮箱古书躲到深山老林里苦读,时隔数年诞生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便是享誉海内外的《篛园札记》。这套书对音韵、训诂、注经、证史颇有见解。所撰石鼓辨证以小学印证古人,又以鼓文勘对史实,广证博考,得到清代国学大师俞正燮的推崇。
我在父亲的案头上见过这部泛黄的名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的版本,厚厚的十几册,比我的年龄还大一岁。后来为了保存这套书,我家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中饱受惊扰。好在我家祖上也就是一个文化家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因而多次运动都有惊无险。
但珍藏这样的书毕竟是要惹麻烦的,和这套书一起的还有一套《何氏家谱》,三个版本,从康熙到民国三十二年版本不等。它用精致香樟木夹板夹着,字是烙上去的,外面裹着红绸布,十分庄严大气。谱中除了记载着何家数十世一脉传承的家族信息,还记载着老祖宗驾鹤西去、皇帝托大臣送来的祭品清单,这在一般的家谱中绝无仅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每逢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父亲和母亲就吓得浑身筛糠,因此这两套书经常转移地方。起初它藏在父亲的书房里。说是书房,其实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有个黄颜色的木头箱子,后来怕有人看到,便把它搬到厨房里藏起来。
我排行老二,姐姐何书香比我大两岁。母亲喜欢叫她大丫头或者小香儿。那天母亲正帮着父亲转移书箱,突然有了临盆的感觉,到医院都来不及了,就把我生在了箱子旁。
说来奇怪,我生下来就睁着眼,冷静地盯着父亲的脸,仿佛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盯得他毛孔悚然,直接不敢看我。母亲把奶头儿塞进我嘴里,然后对着父亲说,这孩子生来跟书有缘,将来肯定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你给他起个有文采的名字吧!
父亲瞅着我歪瓜劣枣般的脑袋和深邃得吓人的眼神,突然觉得很滑稽,无声地咧开嘴笑了。我竟然赶在这样的场合呱呱坠地,头上顶着草,身上沾满灰尘,狼狈不堪。而唯一让二老欣慰的是,我来到这个黑咕隆咚的世界时竟然不哭不闹,吃饱了奶便安静地躺在那里,仿佛那是张舒服安逸的大床而不是只书箱。
后来母亲说我经常在夜里哭闹,但无论怎么哭只要一放到老祖宗的书堆里便安静极了。父亲大声地笑着说:“这孩子跟书有缘!大丫头叫书香,老二就叫书盒吧!但愿他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继承何家的文化传统,光宗耀祖。”
生下来一百天父母抱着我到南门里的大光明照相馆照百岁照,当着摄像师的面我非要吃奶。母亲那时候才二十岁,年轻漂亮,当着男人的面不好意思解怀,我就不依不饶地哭,直到母亲心一横破了例。摄影师很有眼光和胆识,趁着我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从此成了母亲的珍藏版。照片上的母亲黑发披肩,胸乳半袒,欲语还羞,美丽动人。
父亲私下里也很喜欢这张照片,但是吃那位摄影师的醋,认为他占了母亲的便宜,板着脸向人家索要底版,反复恫吓人家,不能翻洗扩印,否则向公安局报案云云。吓得摄影师脸都惨白了,发誓现场冲洗,父亲当面带走底片云云。父亲这才满意地取了照片,吹着《梭罗河》的口哨回家。
父亲在这张他最满意的照片后面抄写了一首泰戈尔的诗:
“祝福这颗小小的心灵,
这洁白的灵魂,
是它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天堂赐予的吻。”
后来他说抄那首诗时欣喜何家终于有人继承家业,心里因为生了个带把儿的儿子而感到特别温暖,但是一想到我的眼神就惊得脊梁上冒冷汗。
后来我向他表明,继承家业我不敢承诺,但至少我投胎投对地方了,投了个书香门第。
事实证明老爸的这个判断是英明正确的,我出生在一大堆泛着书香的古书旁,受此熏陶,从小就爱学习,连模样都长得文静。后来渐渐长大了,更是白面书生一个。母亲回忆说,我最后跟她一起到女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是五岁,按常理,本该我多看几眼那些美丽而千奇百怪的胴体,不料却遭到了女人们的围观,因为我长得又白又水灵,像个瓷娃娃。女人们都忍不住伸手摸一摸我的皮肤,看是不是水做的。庄宝盒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就曾惊讶地说:“你家孩子是咋生咋长的,像白面馍馍,是不是胎里做了手脚?我家宝盒子咋就又黑又瘦,简直就是没发好的地瓜面窝头。”
榆叶这个比喻没有一点儿的夸张,地瓜面窝头是那个年代的主食,整个国家刚刚从苏联老大哥的勒索中缓过劲儿来,有吃的就不错了。关键在于她生了这么个丑陋的孩子,却没有一点内疚。在她看来,模子是好模子,儿子生得丑,完全是男人下的种不好或者说生活条件不好造成的。
事实证明庄宝盒母亲怀他的时候,的确没好好考虑过优生。老庄从部队回家探亲,榆叶去车站接他,半道上老庄就憋不住了,拉着她钻进了地瓜沟里。事毕,女人的屁股让叶茎汁液染黑了一大片,好几天洗不下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瓜沟里下的种自然长得像地瓜面窝头。
他比我大两个月,却矮我一头。脸黑黑的、瘦瘦的,皮肤粗糙。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盘腿坐在炕头看杨柳青的年画,比着画上的胖娃娃生,因此我生下来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脸蛋胖嘟嘟的,眼睛水汪汪的,简直就是画里那个骑在麒麟上的童子。老庄认为,怪就怪宝盒这孩子生在缺氧的高原上,身子没能完全地发育起来。他说部队平常煮饭都是七成熟,这孩子选那么个地方出生,没成个傻瓜就烧高香了。
老庄这话说得有些扯淡,庄宝盒一点也不傻。别看他其貌不扬,但却绝顶聪明,心眼儿多出我不止一个。榆叶说,他两岁还不会说话,只知道淘气。渐渐长大以后,他也似乎不善于和成人打交道,在学习新事物上也不用心。我用了三个月就赶超了他的身高和体重,但智商赶上没赶上没法儿判断。那时候还没有婴幼儿智商测评系统,即便有也用不上,都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欧洲种群和亚洲种群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铺陈这些纯粹是多余,我和庄宝盒本来没有半点牵涉。他远在大西北,我生活在内地。然而,正如毛主席语录中所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父亲一次偶然的决定或者说老庄一次偶然的闹情绪,把我们两家联系在了一起。我和庄宝盒成了同学和邻居。
那一年我俩都刚满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