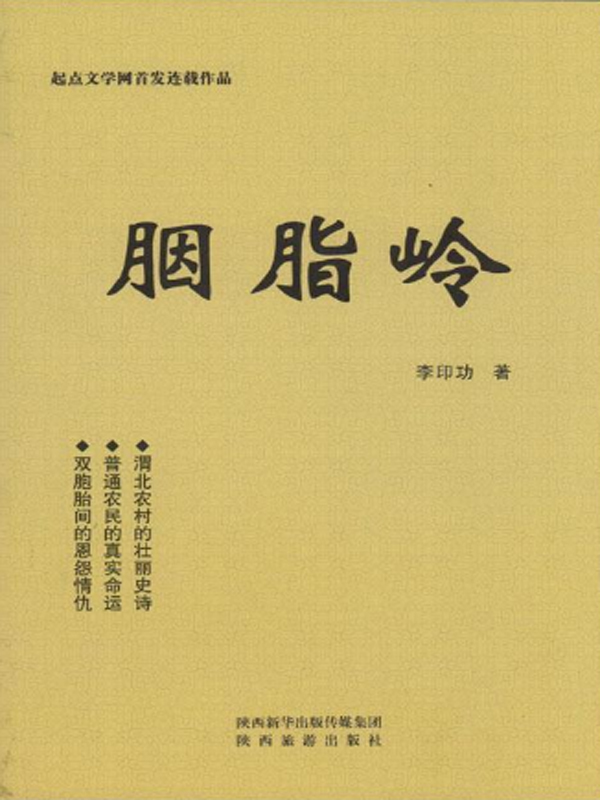
-
胭脂岭
本书由鹿阅读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 1 章节
胭脂岭
李印功
光棍陈黑顺压根没有想到自己在村外的地边尿了一泡尿,落了个耍流氓的名。寡妇刘翠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无意间看见了陈黑顺尿尿,落了个不安分的名。陈黑顺和刘翠花因“尿尿流氓案”上了批判会。
大队书记张金柱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张金梁会把批判对象刘翠花娶回家,刘翠花成了自己的弟媳。还有更多的没想到,让胭脂岭上演了情仇爱恨的大戏!
上篇
(一)
渭北旱原的北部,有一座其貌不扬的土石山岭,一点灵气也没有,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山岭上只有零星的树木和低矮的杂草。杂草生长懒散,不修边幅,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树木东一棵西一棵地分布着,斜身歪脖的,在薄薄的土山皮中拼命地汲取着营养。在杂草树木间飞来穿去的山鸟,发出啾啾的叫声,把漫山遍野的野韭菜啄噙得叶烂茎断,体无完肤。其貌不扬的土石山岭,却有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名字:胭脂岭。胭脂岭前的村堡也因此而得名,有了山和村同名的奇特事。
胭脂岭大队(当时的农村建制,几个自然村为一个大队,大小不等)有三个南北巷道和四个东西巷道,分北、南两个生产队。窄小坑洼的巷道,散落着残枝碎叶,粘在地上发干变硬的狗屎鸡粪,发出刺鼻的气味。门前院落的柴禾堆下,不是蜷着补衣服嚼舌头的老婆,就是钻着翻开裤腰捉虱子的老汉。低矮破旧的民房,担撑在被雨水冲刷得伤痕累累的土墙上,诉说着岁月的辛酸。墙根溃烂,蚁窝遍布,不由得让人为民房的随时坍塌担忧。人的肚皮填不饱,头发稀落,眼袋发肿,满脸忧伤,走起路来像打摆子。牛跟着人受罪,犁地时有气无力,尖瘦的屁股挨了数不清的鞭子。连树都是皮干枝细叶黄,风吹过来懒得摇动,没到落叶的季节就投机取巧把叶子打发掉了,以节省营养熬过寒冷的冬季。整个村庄,与景色和活力无缘,像一个久病的迟暮老者,奄奄一息地躺在贫瘠干瘪的土地上呻吟,随时有可能撒手西去。
到处冒穷气的胭脂岭大队,却泛涌着政治燥热。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金柱亲自上阵,带领十个青壮劳力,花了五天时间,在胭脂岭半腰的山坡上,用白石灰刷写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几里路外的人都能看见,创了全县标语宣传之最,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扬,却招来了社员们的唾骂。有人反映,在唾骂的人中,就有张金柱的双胞胎弟弟张金梁,还有外号“怪怂”的北队社员陈黑顺。这让张金柱难以接受。就在张金柱动心思咋样收拾这两人的时候,一天大早,反映问题的人又告诉张金柱,出大事了。张金柱问:“出啥大事了?”反映问题的人手指半山腰,张金柱一看,农业学大寨变成了“农业学太寨”。张金柱眉宇间起了疙瘩:昨天下午还好好的,一个晚上,“大”字咋就突然变成“太”字了?这分明是有人蓄意破坏农业学大寨,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张金柱派人上山铲除多出的一“点”,找副书记张宽升商议对策。张金梁和陈黑顺自然就成了怀疑对象,在社员们中传得沸沸扬扬。
张金梁和陈黑顺臭味相投,是一个人品。听到社员们的议论,两人在巷口的秋雨中碰见了。陈黑顺把张金梁拉到没水的地方,自己的一只脚伸进一个小泥窝里,踩了两下,鞋帮上满是泥水,他又把露出的裤带头塞进腰里,系了系,两个裤管一样齐了,才说:“咱两个成了胭脂岭大队的‘四类分子’,狗拉的屎都是咱俩拉的,谁给山上标语的大字加点了,干部怀疑是咱两个干的,你说咋办?”
张金梁转身看了一眼山标语,笑了,说:“这谁想得怪,一个点加的,就把人糟蹋了。”说完嘴里嘟囔:“没粮吃,没钱花,学狗屁哩,学啥大寨……”张金梁答非所问。
陈黑顺问:“你说咋办哩?”
张金梁说:“他爱说啥说啥,怂管!我给你说的事,你去不去?”
陈黑顺抬头望望天空,说:“天还晴不了,我家房子漏雨,要修,不想去。”
两个人各自离去。
陈黑顺回到家里,给漏雨的房顶苫了塑料布,用砖头压了四角,又想出门去透透气。他嘴里叼着烟,向村外走去。
多年不遇的秋雨,淅淅沥沥,下开了就收拢不住了,下得房屋渗漏,墙头发软,整个村子,地面上到处是黄泥水,连空气都湿漉漉的。陈黑顺出了门,一边抬脚拣干处走,一边转身看跟在身后的黄子狗。黄子狗喷喷鼻子,摇摇尾巴,跑到一棵树下,屁股对着树身,撒了一泡尿,两只后爪向树身刨了几下土,土就粘在了树身上。
陈黑顺看了看黄子狗,信步走到村子外的玉米地边,站在地垄上,四处张望,自己也有了尿感。他解开裤带,才想起自己嫌洗了的内裤潮湿干脆没穿,这倒省了一道手续,便面朝玉米地里尿尿。按自己的年龄,本应是压着压着就尿到墙上去的,却抬着抬着尿就落在了脚面上,而且尿线细而无力,尿不净。尿完了,刚提裤子,又想尿了,紧掏慢掏,余尿就落在裤子上。裤裆里总有一股尿骚味。陈黑顺无奈地咧咧嘴,脸上掠过一丝苦愁,捏着蔫头耷脑的“老二”惩罚性地抖落,一不小心,裤子唰地落到了膝盖下。弯腰提裤,双脚陷进稀泥里,用力抽左脚,右脚下陷,抽右脚,左脚下陷,腰子一拱,双脚齐抽,“扑通”一声,仰面倒在地上挣扎,活脱脱一个泥猪。
寡妇刘翠花从娘家回来,腋窝里夹着包袱,深一脚浅一脚避着水窝,从转弯处闪过,走到了陈黑顺跟前,看到了这一幕,不由得“呀”了一声,羞得手捂双眼,转身就走,不料脚下一滑,摔倒在泥池里,包袱掉在了水中。
陈黑顺闻声望去,一愣,顿觉尴尬,手撑地站起,说:“翠花,你……”说着走向刘翠花,要拉刘翠花的胳膊。刘翠花蹲坐在泥池里,咋也站立不起,涨红着脸,推开陈黑顺的手,说:“流氓!我不要你扶!”
陈黑顺说:“哎,我咋流氓了?我好心扶你,我还成流氓了?”
刘翠花捡起包袱,抡抡包袱上的水,剜了陈黑顺一眼,说:“你连裤子也不提,不是流氓是啥?”
陈黑顺这才发现,忙于扶刘翠花,忘了提裤子。
陈黑顺就是陈黑顺,偏不忙于提裤子,却心中窃喜,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他脑子里闪出了刘翠花不愿嫁给自己的往事:前几年,我家穷得叮当响,和我一般大的人,娃都跑得咚咚咚,我还是光杆司令。听说你大(陕西方言:指父亲)戴着‘四类分子’帽子,你嫁不出去,我托人说媒,你却狗眼看人低,嫌我家穷,看上张金柱,人家张金柱心高气傲不要你,你偏又嫁到胭脂岭,结婚不久男人死了,又和张金梁眉来眼去。哼,机会来了,叫我报了一箭之仇再说!想到这里,陈黑顺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坏笑,双眼眯斜,说:“你先别管我提不提裤子,你先给我说清,我咋流氓了?”
刘翠花把脚挪到干处,说:“你见我过来了,你脱了裤子把……把……掏出来干啥?”
陈黑顺说:“哎吆吆,我说你是寡妇当得时间长了,见了男人脱裤子那么敏感的?我正尿尿哩,不小心滑倒了,我就知道你过来呀?再说,你明明看见我尿尿哩,你为啥还硬往过走,是想……”
刘翠花撇嘴:“是啥好东西,没见过。我才不想哩。”
陈黑顺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想,谁信?嘴硬哩。”
刘翠花说:“你个瞎怂!多亏当年没跟你!”
陈黑顺说:“当年跟了我,没今个的事了。你干吃枣还嫌核大,免费看了我的……占了便宜,我没寻你的事,你还寻我的事哩。”
刘翠花弯腰在地上抓了一把泥,朝着陈黑顺的脸摔了过去,说:“我叫你胡说!”
陈黑顺提着裤子一闪,从身后刚要抱刘翠花,刘翠花一跑,两人都摔倒在地,泥水四溅,惊得黄子狗四蹄抓地,嗷嗷直叫。
正在这时,满脑子是“谁会给大字加一点”疑问的张金柱,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走了过来,大喊一声:“干啥哩?”
陈黑顺和刘翠花慌忙站起,浑身泥水,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再看张金柱,不知如何是好。
张金柱本来就紧绷的脸皮抽搐了一下,用警觉的眼神打量着两人,厉声说:“大白天的,一个光棍,一个寡妇,跑到村外野来了?伤风败俗!”
刘翠花眼神怯生生地看着张金柱,擦拭着包袱上的泥块,结结巴巴地说:“书记,不是你说的那样。”
陈黑顺抹了一下脸上的泥水,手在裤腰间挖抓,说:“你别拿大帽子胡抡,冤枉了好人,是她故意骚情哩……”
张金柱立马拉下脸,说:“你是好人?提着裤子嘴硬哩。”说话间,张金柱一个箭步走到陈黑顺跟前,右手抽走了陈黑顺的裤带,陈黑顺冷不防,裤子又落下了膝盖,露丑了。
陈黑顺一边忙提裤子一边喊:“你拿我的裤带干啥?”
刘翠花羞得手捂眼睛,转过身。
张金柱没有回答陈黑顺的问话,嘴里说:“刘翠花,你先走。”却在心里说:“你这德性,当年还叫人给我提亲哩。张金梁脑子叫狗吃了,看上你,和你勾搭,都辱没了我家的门风,我要叫他死了这条心。”
刘翠花瞥了两人一眼,紧步走了。
陈黑顺伸手要裤带,张金柱没有给的意思。陈黑顺两手提着裤子。
张金柱一脸威严,说:“我才准备寻你哩。”
陈黑顺问:“寻我有啥事?”
张金柱咳嗽了一声,说:“队长董双奇说,你包着给生产队出牛圈哩,不吭不哈旷了三天工,牛圈的牛粪把牛都快闷死了,你干啥去了?”
陈黑顺一脸的不屑,想答不想答。
张金柱追问:“干啥去了?”
陈黑顺眯着双眼,侧目而视,闷不作声。
张金柱呵问:“说话!”
陈黑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摸黄子狗的头。黄子狗温顺地舔陈黑顺的手。陈黑顺还是一声不吭。
张金柱有些发青的脸上,皮肉抽动,眼神冷峻,把手中的裤带在空中一抡,说:“你不给我一个人说,就在批判大会上说。”
陈黑顺不吃这一套,手搭在脖子上一拉,说:“头割了碗大个疤!”脚踩在水坑里,扑哧扑哧走了。
张金柱说:“陈黑顺,你走着瞧,我就不信,顺不了你的毛!”
陈黑顺给张金柱装了一肚子气。张金柱看看手中的裤带:“哼!耍流氓了还这么嚣张,不做个娃样子,你不知道阎王爷是四只眼!”
陈黑顺突然转过身,瞪了张金柱一眼,把裤腰提了提,撇过来了一句:“当书记闲得没球事干了,连老子在那里尿尿的事也管了!下回我想尿尿了,你给我划个专用场地,派几个民兵给我站岗放哨,三百米以外就让女人绕道走!怪球事!”说完转过身走了。
陈黑顺的话激得张金柱怒气冲冲,走路也带了劲,两脚踩到泥坑是泥坑,踩到水池是水池,鞋湿了,裤腿上溅满了泥点,径直向大队部走去。
大队部在两个生产队的中间地带,是一座三间拱脊厦房,里面摆着一个单人桌子和十几个条凳,是大队开干部会的地方。拱脊房的前面是四间厦子房,一边是书记的办公室,一边是空房子。书记办公室的墙正中贴着毛主席画像,画像的两边是两条标语:一条是“阶级斗争月月讲毫不含糊”,一条是“资本主义尾巴天天割绝不手软”。空房子里搁着大队文艺宣传队的舞台布景和锣鼓家伙。
张金柱推开大队部办公室的门。
正在办公室找人谈话,调查为大字加“点”的副书记张宽升,见张金柱满脸怒气,心生狐疑,问:“出啥事了?哪儿来的裤带?”
张金柱没有回答张宽升的问话,把手里的材料和裤带往桌子上一摔,看了和张宽升说话的人一眼。说话的人,侧身绕过桌子,有眼色地走了。
张金柱问:“调查得咋样了?”
张宽升说:“对在山上写大标语反感的人不少,骂的人也多,不光是张金梁和陈黑顺。说张金梁和陈黑顺给大字加点,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张金柱迟疑了一下,这才把陈黑顺和刘翠花的事说了。
张宽升说:“这事值得把你气成这样?”
张金柱说:“胭脂岭是社会主义的胭脂岭,不能容忍这种乌七八糟的事存在。通过这件事,兴许是个突破口,能把涂改标语的事弄出来。”
张宽升不以为然,欲言又止。
张金柱问:“那你的意见呢?”
张宽升说:“男女之间的这号事,看见了当没看见就过去了,大动干戈,就像擀面杖搅醋瓮,越搅越酸。再说,又没形成啥后果……”
张金柱打断张宽升的话,呛道:“你的意思是出了强奸犯再管?那就迟了!你给我当副手,可不能两手拿泥页——遇事抹光墙!”
张宽升的脸唰地红了,不再说话。
张金柱说:“你去通知开大队干部会,也叫北队队长董双奇参加。”
张宽升不情愿地走出办公室,去通知参加会议的人。
张金柱拿出一张纸,写写画画,记着开会的事项。
张宽升走出大队部,满脸的不高兴,直摇头,心里很别扭:刷个标语,出了个加“点”的事,还没把加“点”的人弄出来,又提个裤带……张宽升带着情绪,通知完了开会的人。
不一会儿,大队治保主任梁明、民兵小分队队长畅亮、妇联主任廖英侠、北队队长董双奇到了,就差大队会计韩结实。他给相好的寡妇乔玲养的母猪配猪娃去了。
会上,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有人说这就是大事,争执不下。张金柱批评那些说是小题大做的人,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张金柱说,就是要善于从小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按自己的意图,安排了给陈黑顺开批判会的事,他要带领大队所有干部坐镇会场,亲自指挥这场批判会。
云层密布,阵风吹过,又下雨了,整个村子被雨幕笼罩。
董双奇从大队部回到家里,问媳妇杨倩






